《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纪中国纪事》第39章 镇反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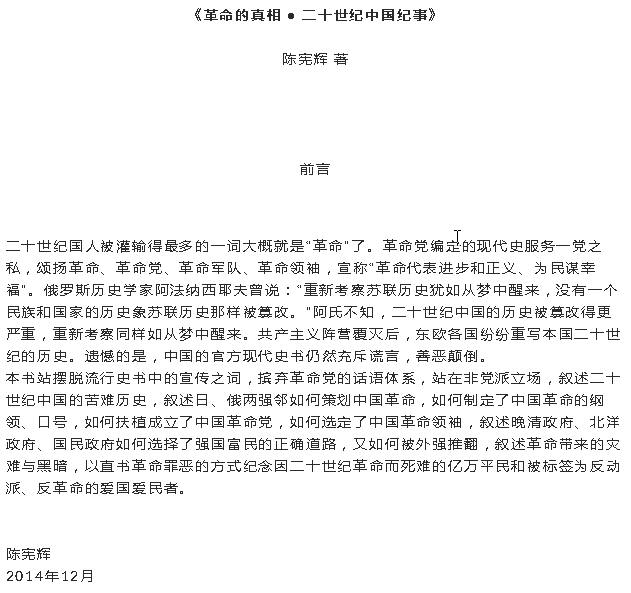
内战中,中共在解放区展开杀地主、剥夺财产的土改运动,引致解放区周边的地主组织还乡团武装报复,中共再以军队对还乡团展开所谓剿匪战。建国后,中共将暴力土改和剿匪战推向全国。1950年3月,毛泽东发出了“镇压反革命”(镇反)的指示,要求掀起杀反革命的高潮。各地中共大员不认为存在严重威胁,没有立即展开屠杀。毛泽东不满,在下令出兵朝鲜的同时主持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双十指示,双十决定),在其中称:“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以至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他要求“纠正过于宽大的倾向”,“当杀者即判处死刑”。两次指示后,各地大员开始了名为镇压反革命的屠杀。个别大员,如华东负责人饶漱石,顾虑商业环境还是没有展开镇反屠杀,被毛泽东点名指为是“对反革命宽大无边”典型(这成为他几年后被清洗的原因之一)。
1951年1月,中南局向中共中央报上了驻湘西27军的镇压反革命报告。该报告说,在湘西21个县,仅仅驻军部队就已经处决了匪首、恶霸、特务4,600余人,并准备由地方政府再杀一批。毛泽东对该报告批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要求“各地务必抓紧照此办理”。1月22日,毛泽东电告华南分局、广东省委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3,700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1] 同月,中南军政委员会报告公安部说湖北省已经逮捕19,823人,其中在省级机关内部逮捕了160人。公安部对报告批示:“如此内外不分地实施逮捕,容易引起广大干部恐慌和思想波动。”毛泽东见报告批评公安部:“湖北做得很好,不要去泼冷水。”2月,西北局向中央报告说:两个月已经逮捕5,000多人,杀了500多人,虽然总体看杀得不狠,处理缓慢;但是执行镇反计划一定要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毛泽东阅此报告后批示:“对判死刑者,轻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 2月中旬,毛泽东致电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大员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南京是一个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不止两百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上海是一个六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两万余人仅杀两百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一年之内至少应当杀掉罪恶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道)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杀掉1500人左右。这个数字是否妥当,请你们加以斟酌。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0人,这个数目太少”;“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说来,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大杀几批,才能初步地解决问题……天津准备于今年一年内杀一千五百人,四月底以前先杀五百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它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2] “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恶霸必须杀掉,否则群众不敢起来。”[3]
同月,毛泽东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其中下达了按人口千分之一比例的镇压反革命指标。这里,毛泽东所言的镇压不是逮捕判刑,而是处决。条例中列举的十二类反革命包括:勾结帝国主义者,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者,聚众叛乱者、参加特务或间谍组织者,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以反革命为目的抢劫、破坏公私财物者,受国内外敌人指使扰乱市场或破坏金融者,伪造公文证件者,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制造和散步谣言者,以反革命为目的偷越国境者,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者等等。毛泽东在条例中将反革命罪规定的尽量宽泛,不区分已遂、未遂,将“勾结”、“包庇”“挑拨”、“传播谣言”、“煽动”、“策动、勾引”等无从界定的随意性罪名都作为镇压的依据。与《惩治反革命条例》中“挑拨”、“煽动”、“对抗”等随意罪名一样,毛泽东指示中的“恶霸”、“民愤”也是随意罪名。
在毛泽东的压力下,各地大员开始突击逮捕、杀人。在北京,公安部长罗瑞卿直接领导、指挥,在2月17日逮捕675人,第二天枪决了58人。毛泽东对罗在北京的做法立即表示赞赏。毛的赞赏让其它地方大员感到压力。3月7日,罗再指挥逮捕1,050人,在3月25日枪决了199人。同月,天津市委向毛泽东报告,说已经处决了150人,拟再处决1,500人。毛泽东再批示:“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京津行动后,华东大员饶漱石为没有展开屠杀作了检讨。市长陈毅向毛泽东报告说:“上海决心在已经捕了1068人,处死100余人的基础上,再放手捕10000人,杀3000,关4000,管3000”。毛泽东复电:“如果你们能逮捕万余,杀掉三千,将对各城市的镇反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你们注意在逮捕后迅速审讯,大约在半个月内就应该杀掉第一批,然后每隔若干天判处一批。” [4] 4月1日,中共上海当局发布了《上海各人民团体关于检举反革命分子的通知》和《关于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布告》,规定:“反动党、团(国民党、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三青团等党派)的干部,国民党军军官,国民党军统、中统等特务组织人员,南京政府所属各组织的成员均须于在规定期限内亲赴公安局设立的‘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总处’办理登记,对有隐瞒,抗拒登记者将予以严惩”。基层负责人不知道高层意图,大力宣传“只要登记、坦白,决不追究”。前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们信以为真,纷纷登记,并说明当年是为了抗日才加入这些党团组织的。然而,当局随后展开了对登记者的捕杀行动,于4月27日逮捕8,359人,于4月30日处决285人,于5月9日再处决28人,于6月15日再处决了284人。上海当局以反革命罪名大规模捕杀有旧政府背景和经历者,对新政权和解放后的经济危机有过牢骚话者,被揭发藏匿武器、散布谣言者,相信当局“不追究”承诺向政府登记参加过与国民党有关的组织者,超额完成了毛泽东下达的指标。
被毛泽东不断点名批评后才展开行动的上海捕杀规模如此,其它城市的捕杀更为惨烈。几个月间,各大城市每隔几天就枪毙一批人,少则几十名,多数百。召开公审大会后立即处决数百人。由于毛泽东一再批评“宽大无边”,各地领导人以多杀来表现积极执行中央政策,对基层报上来的杀人名单一律照准。各地领导人知道,他们头上的乌纱由毛泽东一句话决定,纷纷主动提高杀人比例。例如,贵州当局将毛泽东下达的人口千分之一比例提高到了千分之三,广西柳州专区提高到了千分之五。一时,报纸上 “坚决镇压反革命”,“某某反革命分子伏法”的报导铺天盖地。报纸报导的只是部分城市镇反的情况,多数城市及农村枪毙“反革命”不登报、不公告,处决人数是糊涂账,很多乡村报送到上级的材料只有人名,没有关于罪行的详细材料。因为基层上报只是为了完成杀人任务指标。在安徽,桐城县当局拟将16名反革命处死,报安庆地委审批,地委审查全部否决退回了报告。然而县公安局看到地委回文,以为同意,竟没有拆开看批文内容即将16人拉到刑场枪决。这16人中有5个伪保长,4个三青团区分部委员,3个宪兵,2个一贯道坛主,6个地主,没有一个人有血债。阜阳专区在枪毙几个恶霸地主时还把同他们睡过觉的几个“破鞋”以“给劳动人民丢了脸”的罪名一起枪毙以凑数。
为推动镇反升温,毛泽东否决了西北局提出的“执行镇反计划,一定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的意见,指示将杀人批准权下放到专署一级。 [5] 各地大员知道毛泽东的意思是进一步下放,纷纷将批准杀人权下放到了县、乡级,部分地方下放给了工作组。镇反运动的判决过程通常与农运中的农民协会杀人一样简单,召开公审大会,台上挂出“人民法庭”横幅,运动主持者将认定的反革命分子五花大绑押上台,有积极分子领喊口号,群众跟随,算是完成了审判,然后就拉人去枪毙。运动中,几乎每个县都有了法场。为增加震慑力,枪毙都让老百姓围观。死难者家属通常为免灾难扩大不敢去收尸。
中共在湘西的所谓剿匪最能说明屠杀之惨烈。1949年10月,为争取国民党“湘西王”陈渠珍投诚,解放军湘西军区(第四十七军)政治部在沅陵开办了“和平军官训练班”,组织国民党投诚党政军人员学习,实施“教育改造”,请陈渠珍来参观训练班。陈眼见训练班不设警戒,允许学员周六回家团聚,学员们贴出学习墙报,写学习心得的情况,决定也向中共投诚。[6] 1950年3月,毛泽东的“镇压反革命”指示下达到了湘西,四十七军向上级报说:“已经镇压了反革命4688人,全区八万土匪、几千在乡旧军官,及恶霸与伪警队伪乡保长等坏分子将近十万,我们经过几次讨论,决定分化瓦解消灭敌人。在这个总方针下作出了杀一万人的预算”。经过几个月的镇反捕杀,四十七军在年底报告中提出准备缩减杀人规模说:“中南局……指示均悉,我们都进行了讨论,并已告各部队和地方,镇压匪首惯匪已收到相当效果,应基本上停止。”[7] 然而,毛泽东阅中南局转来第四十七军的镇反报告后,将湘西杀人数与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比较,指责指责华东几个人口大省总共才处决了三千人杀得太少,将四十七军的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负责人,在批示中说:“在湘西二十一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四千六百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使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11] 各地接到指示,以四十七军为护栏,将对旧政府党政军人员的屠杀再升级。四十七军得知毛泽东的指示后变缩减为扩大。在沅陵的屠杀行动中,四十七军组织了几万人参加的公审处决汪援华、潘壮飞、周振寰的大会。汪援华,永顺县人,历任国军团长、副旅长、副师长,在1937年上海淞沪保卫战中率领特务营在浏行地区激战五天五夜,被《中央日报》以《浏行喋血记》为题报道了英勇事迹,1949年率部向中共投诚,并动员其所部暂四师暂五师、国民政府永顺县长、八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周振寰率部投诚。潘壮飞,早年在唐生智部下任团长、副师长等职,抗战中参加南京保卫战,1949年率部向中共投诚。这次公审大会上处决的三人都是投诚人员,并都曾获得解放军“保证生命安全”的承诺。[8] 四十七军将湘西三个专区及所属各县在押的三万多所谓匪特、反革命分子杀了两万多,将几个月前在“和平军官训练班”写学习心得的国民党党政军投诚人员基本杀光,按照送投诚的国民党军到朝鲜战场当炮灰的中共内部既定的处置办法,将余下的数千投诚国民党军送去了朝鲜。[9]
镇反之后,中共湘西在土改和土改复查中继续屠杀地主,被杀害者数以万计。解放军中南军区在部署剿匪的军以上高干会议上提出:“匪患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是农村中地主阶级与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的结合,抵制征粮、反对减租退押、反对土改的严重问题。”[10] 中共内部的说法证明,所谓剿匪实际是屠杀抵制暴力土改,暴力征粮的农民。建国三年后,中共宣称彻底消除了绵延几百年的湘西匪患。新中国长期宣传的湘西剿匪实际是在350万人口的湘西地区屠杀了数万旧政府时期的党政军人员和反对暴政的农民。1979年,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下达了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指示,湖南当局重新审查后宣布,被处决的沅陵“和平军官训练班”成员基本都是冤案,为在镇反运动中被杀害的四万多人平反。
从湘西看全国,镇反运动中受害最深的是两百万国军抗日将士和一百万国民政府基层人员。中共在镇反运动杀害的242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是曾经的抗日将领。他们中包括:何海清上将、宋鹤庚上将、夏之时上将、邓玉麟上将、糜藕池中将、谢崇阶中将、彭旷高中将、崔世昌中将、倪弼中将、曹勖中将、赵世玲中将、周址中将、林伯民中将、田西原中将、李强中将、马守援中将、刘晴初中将、潘峰名中将、宋士台中将、金亦吾中将、武庭麟中将、欧阳珍中将、陈光中中将、陈宏谟中将、陈春霖中将、罗贤达中将、戴炳南、周磐中将、黄镇中中将、徐经济中将、夏炯中将、胡栋成中将、柏辉章中将、钟祖培中将、高倬之中将、黄祖埙中将、黄质胜中将、宋天才中将、李本一中将、李继龙中将、李楚瀛中将、杨垕中将、杨永清中将、何大熙中将、张卓中将、杨清海中将、张乃葳中将、张占魁中将、张国勋中将、余安民中将、张经武中将、陆荫楫中将、习自强中将、王春晖中将、王继祥、邓子超中将、甘芳中将、石毓灵中将、田载龙中将、包善一中将、汤毅生、刘进中将、刘召东中将、刘孟廉中将、刘邦俊中将、刘秉哲中将、刘培绪中将、危宿钟中将、阮齐中将、颜仁毅中将、廖卓如中将、廖士翘中将、廖泽中将、喻英奇中将(南京保卫战中负伤,用蒋介石颁发的一万银元慰恤金创办了“保靖英奇小学”,请于佑任题写校名)、粟廷勋中将、韩起功中将、韩步洲中将、蒋在珍中将、段树华中将、梁顺德中将、陈应龙中将、裴元俊少将、谢灵石少将、鲁坚少将、褚怀里少将、蔡洪范少将、谢东山少将、蒋作均少将、韩子佩少将、韩进禄少将、蒙自仁少将、路可贞少将、廖开孝少将、廖剑父少将、谭化民少将、谭呈祥少将、潘琦少将、樊明渊少将、赵俊图少将……百万国军将士有幸挺过了艰难抗战,看到了抗战胜利,却不幸成为中共屠刀下的冤魂。六十多年后,中共举行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找了一些老兵参加典礼,颁发奖章,为自己营造抗战领导者形象。然而被掩盖的事实是,真正抗日国军早已在建国之初被大规模屠杀,中共对此三缄其口,全无谢罪,更谈不上赔偿。
百万国民政府人员中,除少数在海外有影响的国民政府省主席、厅长以上的高官为“统战”目的不杀外,其余都成了镇压对象。发动“渡江战役”前,毛泽东、朱德曾联名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在其中承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除战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散兵游勇投诚报到者概不追究”。准备逃走的旧政府、旧军队相关者及富人们相信了安民告示,留下来归顺新政权。他们没想到,中共建国不仅不循历代开国大赦天下之例,相反将国民党政权基层官员及雇员中的大多数以“反动军人”、“特务份子”、“反动党团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罪名关押或枪毙,将乡长、保长、甲长、村长等旧基层人员几乎斩尽杀绝。例如,国民政府贵州的81位县长全部被中共杀害。旧政府基层官员中的幸存者多数没有躲过随后的肃反等运动的打击。到文革时,与旧政府相关的人员基本消灭干净。害命之外还要谋财,中共中央在镇反运动中发出了《关于没收反革命份子财产的通知》,要求没收被镇压、关押者的财产。
大规模的镇反屠杀是毛泽东一手推动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充斥关于要求放手杀人的指示,充斥“应当放手杀几批”、[12] “已杀七百,拟再杀七百左右”、“应坚决杀掉”、[13] “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14] 等血腥字眼。与镇反运动同时的土改运动也是毛泽东一手推动,也是杀人如麻。如果加上同期镇压旧政府党政军人员和抗争农民的“剿匪战”,中共建国后几年的血腥超乎时人和后人的想象,是古今中外政权更迭中最血腥的记录。血腥屠杀之外还有更大的迫害数字。两百万被杀害、关押的旧军政人员之外,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孩子被株连,受到长期迫害。四十年前,袁世凯在政权更迭时申明“饮水思源”,“政非旧不举,人非旧不用” ,“优容前清耆旧”,最大限度地避免流血,创造了政权更迭最少流血的记录。民国后,中国经历了多次政权更迭,通常是旧军政首领通电下野出洋为止,大多数低层职员照样效力新政府。了解了中共建国后的血雨腥风,人们才感到袁世凯政治家风范之伟大,才感到清末、民国时代的宽容。
1952年底,中共宣布镇反运动结束。由于镇反运动后期毛泽东重施延安整风后期批评“运动过火”的故伎,指责地方官员滥杀,各地官员跟随毛泽东转向,从多报杀人数邀功转为少报杀人数免责,镇反运动的死难人数被大幅隐瞒。关于镇反运动中的死难人数,蒋介石的一篇谈话可作参考。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计划,是要在一夕之间,把一个重人道和以忠厚宽大做传统的民族,变成一架战斗争杀的机器。我在下面只将共党自己公布的两套数字给你。第一套数字是根据各地共党军政委员会在1951年10月初所作的正式公布,北平政权在1949年10月1日与1950年10月日之间所清算的‘反革命份子’为数达119万人;第二套数字,系从北平的《人民日报》,上海的《解放日报》,广州的《南方日报》和汉口的《长江日报》等四种共党机关报纸所发表的新闻中统计得来,在1951年2月与1952年2月之间,它们所发表被清算的非共人士共为383万人。这与第一套数字合计,共党自己承认的人数,已在500万以上。但此种计算,自然并不完全,因为就第一套数字而论,我政府还不曾获得共党华北区、东北区和西北边远区军政委员所发表的报告。就第二套数字而论,报上所载的数字,也不过是一部份。1952年1月以后,共党反复不断举行大规模之清算,一定比上述数字要超出很多倍。”[15] 陈诚抨击中共以人民和革命名义屠杀的逻辑写道:“黄巢闯献嗜杀,并不讳言嗜杀,张献忠且不惜立碑以表扬其嗜杀。唯共党则不然,共党杀人,明明是师承列宁、斯大林的恐怖主义,以遂行其血腥的独裁统治,却往往饰词造说以相掩饰,并多假托人民公意以行之,这种欺人自欺的手法,不但残酷,而且卑鄙,以视黄巢闯献虽凶残而尚能表里如一者,就‘匪格’言也要定属下下。所以吴稚晖先生批评共党,说他们‘好话说尽,坏事做完’,最为要言不烦。” [16]
中共对旧政权人员的屠杀是苏俄引入中国的革命祸害,苏俄就是这么作的。俄国革命前,沙皇流放煽动罢工的列宁时堪称优待,没有集中营和监狱,仅是流放到指定地区,列宁在流放地不受任何限制,不需要作任何工作,有家属陪同。十月革命后,列宁下令将已经退位的沙皇罗曼诺夫皇族及亲王四人斩尽杀绝。杀皇族仅是苏俄红色恐怖的开始。列宁要求“对阶级敌人实行恐怖行动”,“在调查时无需寻找证据证明被告在行动上或语言上是否反对苏维埃政权”,[17] 声称“无产阶级的专政就是不受任何约束,不受法律条文限制,没有规章制度制约,完全是以暴力为基础的,没有哪个领域是肃反委员会不应该涉入的。”[18] 他下令所有农民必须交出多馀的粮食以换取收据,将抗拒交粮者就地枪决。时任苏共司法委员埃萨克.斯坦因倍格披露,列宁提出一项法令草案,标题是“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殆中”,其中有一条,要求把一大批犯人不经过审判即以敌特,投机商,盗贼,流氓无赖,反革命煽动者,德国奸细等罪名“就地正法”。斯坦因倍格反对恐怖道:“那末,我们何必还要什么司法人民委员部?让我们干脆把它叫做社会灭绝人民委员部,把社会上的人统统斩尽杀绝好了!”列宁回答:“这正是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我们却不能把它说出来罢了。” [19] 列宁要求杀人的指示,命令不胜枚举。例如,“同志们!五个县区的富农暴动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把那些臭名彰著的富农、财主、吸血鬼统统吊死,人数不得少于一百名(吊死后就挂在那里示众,让民众观看) ……把他们的全部谷物,统统没收过来;要指定一些人做人质——照昨天的电令办理。要做到这样的程度:使周围数百俄里(公里)以内的民众都能看到,都能知道,都会胆战心惊,奔走相告,说我们正在绞杀那些富农吸血鬼,而且还要绞杀其他的吸血鬼。”[20] 建立红色政权后的几年中,苏俄成立了数百肃反委员会(契卡)和一千多个革命法庭,以反革命罪名杀害了数百万人。苏共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晚年回忆:“契卡和克格勃人员曾在签署枪毙名单时展开‘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比谁签得快、签得多。无数死刑判决书上仅写了俄文枪毙一词(расстрел)的第一个字母P。日托米尔州一个叫维亚特金的人不经侦讯和审判就擅自决定枪决了3000人。”[21] 屠杀之外,苏共没收被杀害者的财产,其中的部分金钱被用于了建立中国共产党。了解了苏共建国后的所作所为就会清楚,中共的镇反照搬自苏俄。对比苏俄的肃反条例、苏共为中共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和毛泽东建国后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会发现,三者一脉相承。对比列宁的“杀死他们”、“统统吊死”、“就地正法”、“人把他消灭掉”、“绞杀那些富农吸血鬼”等字眼,毛泽东的镇反指示又是一脉相承。民国时的张作霖,对苏决裂后的国民党政府谴责赤祸没有错,新中国的镇反运动完全是苏共镇反的再现。
镇反运动中,中共发展出了两套迫害人的制度。其一是管制制度,中共将幸存的国民政府公职人员和旧政府雇佣杂役,国民党员,与国民党人有关系者,有直系亲属在镇反中被杀或外逃者,集体加入过三青团者,曾经脱离共产党者,曾为国民党报纸撰文者等等数百万人列为“有历史问题者”、“内部监管对象”,对他们实施长期监控,要求他们经常向公安等“管制部门”“报到”,逢年过节和政治运动期间要接受当局训话,走亲访友,参加聚会要向当局申请批准。其二是苏俄引入的政治档案制度。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共要求干部写自传,写交待材料,填写各种表格,以这些材料作为整人手段。整风运动后,每个干部都有了自己看不见的政治档案。经过镇反运动,中共将政治档案制度由党内推向全社会,给每个人建立了一份本人看不到,无法申辩、澄清的政治档案,将全体人民都纳入了中共政治审查和监视体系。在随后没完没了的整肃运动中,人们的政治档案被塞进了越来越多的东西,包括党团组织的鉴定,被要求填写的各种表格,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别人写的揭发材料等等,甚至包括了日记、信件,男女私情等隐私材料。在确立党国体制后,中共营造了百姓没有政治档案就无法生存的环境。很多人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后才知道自己蒙受了长期的冤屈是因为政治档案中被塞进了诬陷和陷害的材料,还有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遭受了政治陷害。






 脸书专页
脸书专页 翻墙交流电报群
翻墙交流电报群